

今年6月,演员陈冲出了一本自传体散文集《猫鱼》,如今63岁的她在书中回忆起自己生活过的几个家:故乡上海在她心中是永远的家,而美国加州则是她生活了多年的家。

21岁那年陈冲去了洛杉矶读书,她从纽约转学到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学习电影制作。那是80年代初,出国前她曾获得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
出生在医学世家的陈冲,因着爷爷和父母都曾经在国外的大学进修和担任做客教授,她在出国前已经会讲流利的英文。出国后她靠着拿奖学金和在餐厅打工来维持生活。为了赚学费,她业余时间开始在好莱坞拍电影,也曾为了拿到一个角色花费全部积蓄请200美金/每小时的老师辅导英文。
陈冲作为演员在好莱坞度过了大半个青春。

《狂想之城》剧照
陈冲:我从1982年到1992 年,其实也就是我大半个青春,在洛杉矶。
马岩松:大部分靠什么呢,靠运气?
马岩松:好的时候那就是特好,人人都说好,不好的时候,就......
陈冲: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所以不好的时候,只要不去看报纸就行了。我现在都很少看网络,噪音大过了真正想听的东西。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对你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马岩松:是自己人性的弱点吧。你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就直接发挥就行了,那个容易点。但是还有弱的地方,反正自己知道,自己老是觉得能看出来。
陈冲:那这必然的。
L.A 或许不能代表洛杉矶



《狂想之城》剧照

1935年即将完工的格里菲斯天文台。图片来源 / Water and Power Associates



《狂想之城》剧照



电影《末代皇帝》剧照,1987


马岩松:感觉经历了好多。
陈冲:对,经历太多了。如果说没有电影的话,我的人生将是非常单调乏味的,然后它的确让我有了表达的机会。因为在生活当中,我比较隐蔽,就在电影当中能够偷偷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能够透露出来。所以有时候虚构可能是最真实的一种东西,因为在它的掩蔽之下,你可以赤裸裸。在生活当中经历过的情感,如果说最欣喜若狂的或者最悲痛的,你就是许许多多的痛苦也好。所有的这种经历都变成了最富有的一笔财富,在电影当中得到安抚,所以这一辈子受益于它。
陈冲:的确是,我觉得做艺术的就是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你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变成了你的资产,它又给了你机会能够演了那么多的角色,可以不承担后果地去体验了许许多多的欣喜也好,痛苦也好,就是给予了你太多。我相信你就是,建筑给你的恐怕也是一样的。人们总是说你为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或者是多大的付出、多辛苦啊,嗯,其实都是它在给我。
陈冲:完全没有。我好像当时跟自己说,28岁这一年必须得改行,因为我觉得还来得及再回学校学一门像样的专业。然后 28 岁那年,还在拍戏。然后到了30岁生日那一天,家里鲜花就布满了,就跟一场葬礼一样,整个房子里布满了花,比人家什么追悼会上的花多了,然后就觉得行,这回可以结束了,因为电影是青春饭嘛,然后我说好,下辈子好好结婚生孩子,可能还能再找到一个另外一件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停了一两年停不住,实在太想念了,觉得自己做不到,离不开电影。
马岩松:我觉得你是挺感性的。
陈冲:我可能都有吧。因为做演员他必须是比较敏感的嘛,必须把自己处在一个比较易受伤害的状态当中。每一个人他都是很丰富的,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无数个人在,只不过就是社会所允许我们的,家庭所允许我们的,或者我们自己所允许我们做的事,只是自己的很小的一部分,非常狭隘的一部分。其实你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了你对善良的可能性,你对阴暗的可能性,所有的都远远超过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人,而所有的角色就给予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去让那些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允许存在的那些人,都让它释放一下,是这样的幸福。
导演:马工,刚刚陈老师的作品在屏幕上就是也是一场造梦。您的作品其实也是,您在给这个城市的人造梦,你怎么看您的作品和造梦之间的关系呢?
马岩松: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挺不一样。做电影就是感觉就老在一个梦里边,一个超现实世界。建筑有点怎么讲呢,我是一直面对这个城市,我觉得整个城市,还有我们生活现实世界就是挺无聊的,可能我是希望能制造一些洞口。刚你说那个爱丽丝,那有点像了,就是让人有机会,如果他愿意的话,能通过这个建筑或者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陈冲:我看到你的有一些设计,我也的确是觉得,就是说路过的人他的确会觉得耳目一新,然后会受到某一种震撼。
马岩松:他至少不能忽视了,即使有的喜欢不喜欢也好,但是他那个感受被调动起来了。
陈冲:其实,人怎么样让他能够集中思想地去看一件东西,在今天这个世界也的确是不容易的。让它能够站在他眼前,看它,仔细地看。
马岩松:我觉得艺术还是想跟人有共振,他想找到这些跟他共振的人,他突然被唤醒了一些东西。
陈冲:有的时候好的电影,它的确是把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或者最微妙的某一些细节无限地放大呈现在你面前,你在生活当中完全忽略了、但是你不应该忽略的东西,它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到了,体会到了。这样的一种注意力,让人去关注到某一个完全被忽略了的细节,这是文学跟艺术,它有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一个城市,坐在公车里面想别的事儿,刷手机,什么能够让他在窗外,然后让他跟着回头看,这个就是有了这样的注意力才能引起他的一种思考。
“进入了自己的想象
![]()


陈冲: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有Frank Gehry建造的音乐厅,我都不知道它是个音乐厅,就路过了,哟,我说这什么呀,就让你目不转睛。他不是原来说是要盖石头的吗?
马岩松:石头的,盖成金属的。
陈冲:然后就是甲方坚持,要金属。
马岩松:坚持对了。这边有了光就更好看了吧。有光照过来,反射上去,冷色、暖色。你觉得它看起来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呀。
陈冲:都有,雌雄结合。
在1992年项目开工后,建造地下停车场的过程中超出了预算,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洛杉矶县议会决定出售政府债券,同时时任洛杉矶市长与加州慈善家艾里·博洛特共同发起募捐活动。得益于这些努力,华特·迪士尼音乐厅才有机会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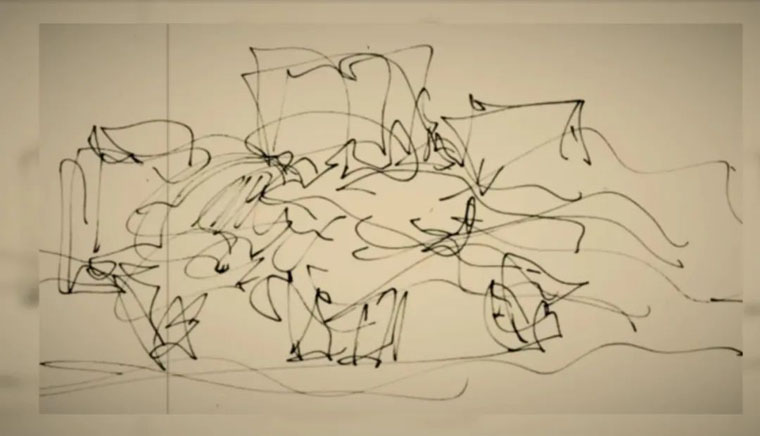
陈冲:你能想象它是石头的吗?好像很难哈。
陈冲:那为什么他说初衷是石头的?
陈冲:每一个角度它都很好看。
陈冲:对,就没一个角度是重复的,没有一根线条角度是重复的。
当初为了把极端的设计方案变为现实,盖里将一个原本用于航天工业的数字化建筑设计软件——CATIA应用于建筑设计中。通过它使得华特·迪士尼音乐厅独特的金属外观和复杂的结构得以精确构建。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内部,图片来源 / Hartwig via Wikimedia Commons
马岩松:这里跟薯条很像,很有动感的一个瞬间,里边有自然光,这很难做到,因为它声音要跟外边隔绝,但是那个厅的几个角是有自然光可以进到室内。里面根据声学(的设计)还挺严谨的。
马岩松:它藏在里边,像那个,还有一些顶光在那上面。这个绝对是进入了自己的想象空间,做梦了是不是,就你看这个实际的时候,你怎么能想到这个。就完全是一想象空间了,然后把这想象空间从脑里拿出来,咔就放在这,无论如何要给他动手,我还是挺佩服他这种勇气吧,就是有时候我们把这脑里想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给他修修修,为了好像是可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它就有点被纠正了,没那么决绝。
陈冲:为什么,为什么还不会被接受?
马岩松:对,他不能被接受,不能实现等等,得失心很重。而且现实确实是,他有很多也建不成,一堆这样的模型可能是,但这个成了。
马岩松:想法又不一样了啊。而且建筑的环境一变,这种反应也不一样。
陈冲:而且自己会变。
马岩松:自己想法不一样。但是其实你没那个想法,后面也不会有那个想法,他反正也是一个人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看以前总是觉得不满意,因为从那过来,但是你没有那块,也没有后边的。
“时间和我们是
作为第一家通过图像叙事的博物馆,卢卡斯谈起为什么选择了马岩松的设计时,他说:“我想让年轻人从远处就能看到这个建筑,然后说:‘我想去那里’。”


导演:陈老师,您今天在电影院说,你觉得特别感谢命运带给你的,这一辈子能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能经历那么多生活。你会认为命运会有一些注定吗?这是一个人创造的,还是说有个更大的意志在?
导演:马工,你呢?因为像高迪也是感觉是,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故事了,很有秘密感,你会有这种想象吗,还是你觉得可以创造?
陈冲:你自己呢?
马岩松: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特别想,也不是那种特别能想清楚或者计划想干嘛的那种,有时候就是一个有感而发,到那时候,就那种很强的一种迫切的东西,就要推着往那走,然后你能接受所有后果。
陈冲:一个小孩问说,哎呀,不要去谈什么爱情了,多痛苦啊。我说你难道不要那个痛苦吗?
马岩松:省得体验了是吗?怕麻烦。
导演:他们觉得不值,你觉得值,得到最多的是什么?
陈冲:生命啊,美丽啊,生命本身。这根本就是生命对自己的欲望。不过也是礼物啦,上苍的礼物。
导演:痛苦也是种礼物吗?
陈冲:你就知道说你还活着,那种疼痛让你很鲜明地知道生命是什么呀。
马岩松:你有没有目标啊?

《狂想之城》剧照
滑板少年:冲浪、滑雪、滑板等等都可以。我在Coco海滩有一栋房子,我时常从那里往返,那里真的很不错。这就是我的全部。
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海滩。
